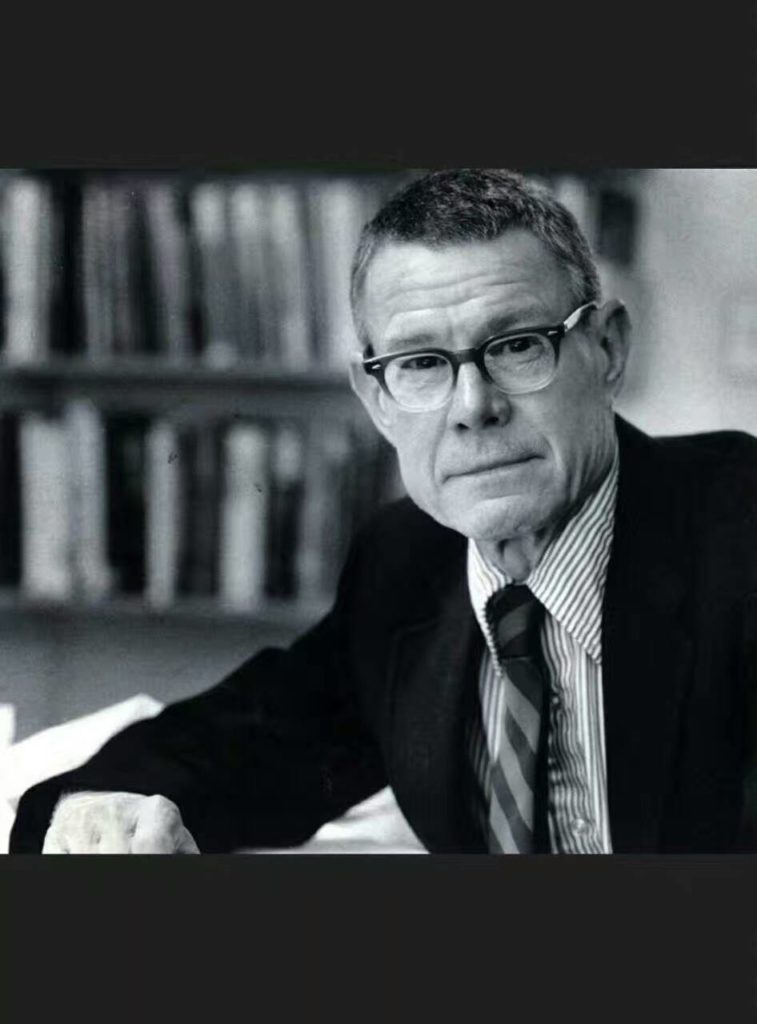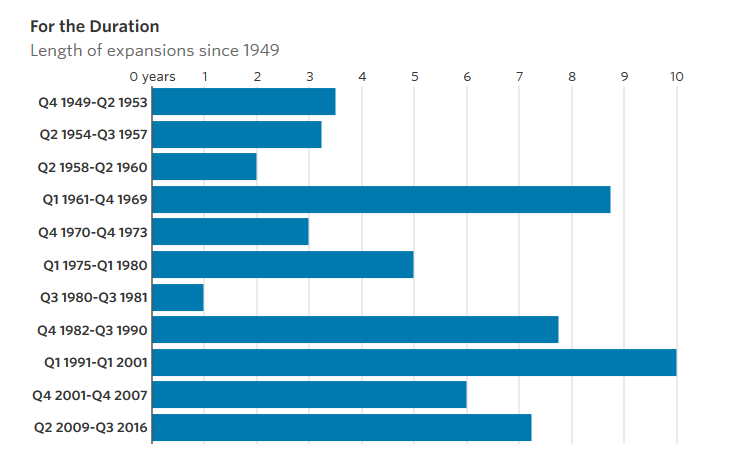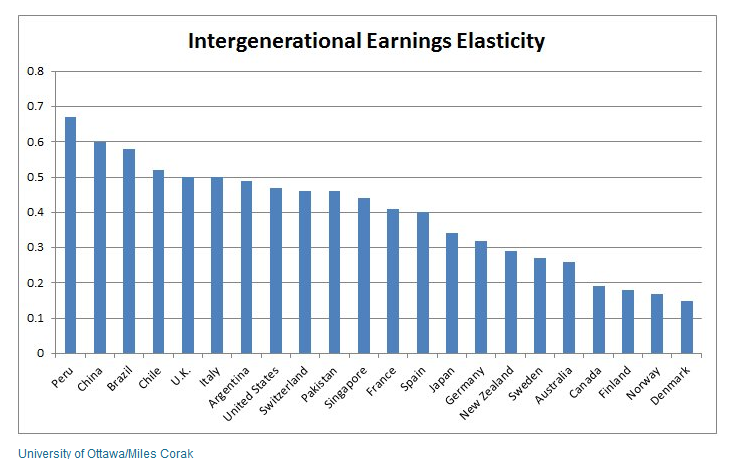前不久反韩运动风起云涌,我的脑子里一直有的一个疑惑又突然闪了出来: 美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没有动用原子弹,而最终签订了停战协定? 是基于道德两难(moral dilemma)吗,还是别的原因?
被我找出了一篇叫“原子弹外交”的论文,是多年前发表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上的,该文参阅了很多美国政府解密的资料,43页满满的。今天周末,和朋友爬完山回来,正好休息研究下。仔仔细细看了我将近一个小时,总算是把谜团解开了。在这里简略和大家分享下。
首先是当时美国的核打击能力。 美国当时拥有二三百枚核弹,在数量上超过苏联一大截。在朝鲜战争开打后不久,杜鲁门总统在公开场合就多次提到过动用原子弹的可能性。讨论结果是如果苏联参战,造成联军溃败,不得不放弃朝鲜半岛时,就考虑核打击。所以动用核武是战略防卫,不得已而为之。
可是误打误撞,中国却意外地加入了战争。说意外,是指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跨过38线向鸭绿江挺进时,过于自信,他向杜鲁门保证中国不会加入战争。可中国的加入搧了麦可阿瑟一记大耳光。麦可阿瑟的误判是美国军史上的一大重大案例,如今还被美国政治系学生广泛讨论。之后,美国又将动用核武对付中国提上日程,首先将B-29轰炸机部署到了关岛,接着又将核打击的几乎所有装备运到了关岛。
朝鲜战争的升级急坏了英国首相阿特利。他不请自到,匆忙飞往华盛顿,警告杜鲁门,不要被麦克阿瑟牵着鼻子走,扩大在亚洲的战势; 防御欧洲,避免苏联红军趁虚而入,才是战略上最重要的。所以,苏联对欧洲的威胁是我们在讨论朝鲜战争中所缺失的。而且不仅在欧洲,美国也非常担心一旦动用核武后,苏联会对保护国日本进行报复性核打击。
接下来,发生了戏剧性大转变。麦克阿瑟绕开杜鲁门直接威胁中国,说中国的装备如何落后,再不撤走,联军将不再克制云云。这下可气坏了杜鲁门,说到底你是头,还是我是头。在美国,军人绕过文人总统直接向对方喊话,可是大忌。图三便是杜鲁门紧急访问他的这位失控的将军。到访以后,麦克阿瑟居然没有向杜鲁门行军礼,而只是握手。 这一细节再次激怒杜鲁门。在朝鲜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之际,麦克阿瑟总司令之职终被免去。
临阵换将,战争大忌,有涨对方志气之嫌。杜氏担心中朝从此有恃无恐,高估自己实力,继续增兵,扩大战局。于是,原子弹外交正式被启动。
美国派密使转道香港,通过那里的联系人,向新中国政府转递信号。 两个目的: 一是向中国言明原子弹巳部署到关岛的信息。由于之前美军过38线的意图已被中国误解,所以这次一定要讲明,怕中国不知道,从而对战争再次作出误判; 二是强调美国完全有能力打击中国重要的战略目标,迫使中国发展几十年停滞不前。 特使再临行前, 一再被交代,和新中国领导人交涉的时候,一定要“委婉“地言明利害。
对中国的威胁其实有bluffing的成分。因为如果美国在中国耗尽了自己的核储备,等于便宜了苏联,也失去了在欧洲有效的核威慑。
历史证明,中国领导人出于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,并综合战争的僵持形式,果断地作出了正确判断,在杜鲁门下台,艾森豪威尔总统上任后不久即签署了停战协议。而之后新中国在内陆大建三线工程,也证明美国的核威慑的确达到了预期效果。而三线工程对我国经济地理和布局都带来了重大影响,直到战争结束60多年后的今天。